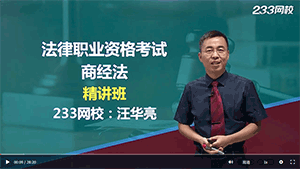(二)恢復利益的可能性
1.死刑是“刑罰”的一個形態。刑法第9條規定的“刑的種類”,雖說作為主刑至少每個種類具有“不同的性質”,但也必須同時在“統一性的原理”之下是可能說明的。因此,由于刑罰的“恢復侵害利益的可能性”的問題,也必須在與其他刑罰之間的對比上研討死刑。
當作此研討之際,關于“生命刑”和“自由刑”、“財產刑”之間的比較,由于刑罰被奪的“利益”上的“價值”(要保護性)有輕重,這一點必須當成理所當然的前提。“生命”優越于“自由和財產”,所以適應它而要求“罪刑之均衡”這點不論從報應和預防的任何一個觀點上都能被肯定。因此,在這里對死刑強調(注:例如,正木,前列注(37)7頁認為“生命的情況比監獄刑的情況也好,比財產刑的情況也好,要發生不成比較的尊貴物質的剝奪,在無可奈何的一點上與其他情況不同。”再有,宮澤浩一譯, 阿爾徒爾·考夫曼《關于死刑》法曹時報1卷7號(1965)1024頁認為:“其他的刑罰至少能夠恢復到某種程度,與之相反死刑是完全不能恢復的。”進而,宮澤,前列注(37)88頁,批判植松博士的見解而認為:“死去和活著,看起來好像是一個階段似的,但實際上它們兩者之間有一個搭不起橋梁的鴻溝。活著的人可以訴說沒有事實根據,然而死去的人卻不能說自己。”另外,也參照前注(40)的遷本教授的見解。)“生命的價值”的“始源性、包括性”這樣的特殊性,盡管這一點作為它本身來說是正當的,但因為它是利益剝奪之差異,也就是“生命的絕對性”的問題,所以在本研討中不得不舍棄。為什么呢?這是因為,該問題是圍繞“個人之尊嚴”的固有的論點,關于它本身,在另外的研討(續稿Ⅲ一)成為正式的需要之故。這樣,首先把考察的對象限定于“由刑罰被剝奪的利益”的“恢復不可能性”予以論述,這作為“問題的限定”并非不妥,作為研討的方法(“講壇”)是能夠容許的。
2.且說,被剝奪的利益的“恢復不可能性”在生命刑上雖然是最大而顯著的,但如果把其差異當作別論,于其本質上在自由刑和財產刑方面也同樣不能否定。假定是這樣的話,關于這個問題,死刑和其他的刑罰雙方本質上沒有差異,所以應該關聯“死刑”存廢的論點就不能產生了。
如果從“個人的尊嚴”出發,“生命”和“自由、財產”兩者是相關性質的乃至補充性質的價值。“生命”是“自由”的才具有意義,利用“財產”得到維持。沒有“財產”(衣食住)的“生命”貧窮脆弱,沒有“自由”的“生命”像不會動的石頭,不過是接近于有機體。相反地“自由和財產”對于死者也是無緣的,以“生命”作為不可缺少的前提才值得保護。
“生命”在時間空間上以有限的“一次性”作為其宿命,所以“自由和財產”是在每一個時間和場所維持和充實生命中不可缺少的。因此,不論是充滿希望的青春時期也好,臨近死期的病人的短暫時間也好,在該時間被剝奪的“自由和財產”也基本是不能恢復的。它并不是依存于期間之長短,效用之大小的。譬如,即使是僅僅一天的拘禁,和他在這時約會見面的人已去旅行,等于是今生永遠不能再會了。就是剝奪財產也能產生同樣的不能恢復,這是很明白的。就是說,“自由、財產”的剝奪也是以“生命在時間空間方面存在的一次性”為其前提的,所以,在此限度內完全是不能恢復的(注:關于這一點,植松前列注(38) 345頁~346頁上,正當地論述說:“說起來,人生是不可逆轉的。 某一期間自由被束縛這一事實,也決恢復不了。進而是,此后一生的經歷不得不改變將來的情況也不少見。在此意義上,自由刑的誤判也不能恢復是很清楚的。即使是輕度的財產刑,到其被證明不實為止,不僅身分受限制,在社會性普遍信用上也受到重大影響,在不同情況下,會變成終于不能恢復的結局。只是,死刑是比財產刑,再是比自由刑是剝奪更為重大法益的行為,如果有了誤判,則其結果是與之相應地重大的。因此,科處死刑必須要比科處其他刑罰更為慎重,這是毫無疑問的,但說成唯獨死刑的誤判,尤其是不能恢復似的說法,這不妥當。”)。
這樣,“恢復現狀(現時的)之不可能性”對于所有的刑罰是共同的,在生命刑和自由刑、財產刑雙方上只能看出相對性的差異。因此,如果從“不能恢復剝奪利益的現狀”來看,在所有的刑罰上,不能不產生“出于誤判的弊端”。在這個意義上,在和誤判之可能性的關系上,沒有理由僅僅區分開“死刑”。
3.對于這樣的結論,將會出現下面這樣的反論乃至疑問。
自由刑的情形之下,第一,如果是其執行終結前的話,由于釋放,能夠回避“超過此刑”的自由剝奪。第二,如果認為財產不外乎是“被壓縮的自由”,把該自由換算成財產,而“事后的補填”將和剝奪財產的情形一樣是可能的。與此相反,生命刑的情況是,任何救濟都是不可能的。對于被殺的被害人來說,就連事后的損害補償都不可能,在這里,死刑的問題是明白的。
盡管如此,這些反論并不是決定性的內容。第一的救濟可能性的差異,由來于死刑和其他刑罰之間的本質性差異。也就是,自由刑和財產刑上損害是部分性質的,在數量性質上能夠計算,與之相反,生命刑卻并非如此。這一點也連系到第二的事后補償的差異。可是,這個差異,只不過是從“生命的尊嚴”這一個后面應該研討的問題里派出生來的特殊性而已。再有,無期徒刑和長期的自由刑的情況下,其執行終結后的“事后補填”未必是奏效的,它和死刑之間的差異再次相對化起來(例如,服刑人在釋放后就死去之類的情況。)不論怎么講,事后性的補填,并不是純粹的現狀恢復,只不過是其代替手段。
從結論來說,不論是剝奪利益的“不能恢復現狀”也好,“不能事后補償”也好,都不僅僅是服刑人特有的問題,也是被害人的共同問題。因此,如果從“報應刑論”的立場來看,只是行為人和被害人同樣應該蒙受剝奪利益而已。因此,這個論點本身,只有在把“回避誤判之不可能性”作為其前提,對無辜執行死刑才具有意義。于是,必須把研討轉移到下面的“誤判”的論點。
(三)回避誤判的可能性
1.首先應把由于刑罰的“不能恢復剝奪利益的現狀”作為前提,研討“不能回避誤判”的問題。在保留死刑論的立場上,由于認為不能恢復剝奪利益的現狀是所有的刑罰上相對共同的,所以即使它和“不能回避誤判”結合起來,也并非是死刑特有的問題(注:前注(38)、(42)中所列學說。另外,高瀨暢彥《圍繞死刑的法制(28)-死刑存廢論會有結果嗎?》搜查研究32卷(1983)11號80頁認為:作為“制度論”的“誤判”正是由于“法院的專權”被決定的,而并不是“客觀性的事實認識的問題。”)。所以,這個問題已經允許從死刑存廢論的對象里取出。就是說,回避誤判,只是作為刑事程序的一般性問題論述就足夠了,關于死刑充其量只不過是把回避誤判的刑事程序應相對地加以強化而已。
與此相反,廢除死刑論的立場則是,應當認為不能救濟恢復剝奪生命是死刑絕對固有的性質,“不能回避誤判”對于審判和刑罰作為一般性的問題是不能容許的(注:參照前注(31)、(37)、(40)、(41)所列的學說。尤其是考夫曼,前列注(41)1031頁認為:“盡管提出誤判是罕見的但情況也好轉不了。1000例,10000例當中, 只有一個人連罪也沒有卻被死刑執行官之手殺掉了,盡管如此,廢除死刑也有充分的理由。”但,重要的是,這將是與其說回避誤判之不能,勿寧說“個人的生命”連必要性都沒有卻被剝奪這是個更為根本性的“生命刑”的問題。)。總之,和自由、財產不同,只有剝奪生命是決不許誤判的。
就是在這里兩種論調也配合不起來,其對立的原因也未必就存在于“不能回避誤判”其本身。其對立的原因在于:把“生命”與其他法益區別開來,是否承認構成生命前提的作為始源性的包括性的利益(注:參照前注(41)所列學說。)。盡管由于誤判,不能回避自由、財產是不得已的,但構成其前提的不能回避生命是絕對不能容許的。是否應該這樣考慮,形成了圍繞死刑存廢的對立。
2.由于誤判,以執行死刑判決而被剝奪的生命,事后不能恢復救濟。可是,就在考慮生命的價值是絕對的情況下,它可以成為廢除死刑的絕對根據嗎?關于這一點,站在保留死刑論立場上的竹田直平博士也展開了如下有力的異論:
“為了避開誤判的危險,不言而喻講求所有合理方法是必要的,但如把它作為理由要求立法中廢除死刑,應該說與因為頻頻發生交通事故而為了避免這種危險,主張全面禁止火車汽車飛機等近代交通工具同樣地,不,比它更加不妥當。(注:竹田直平《死刑(第32條)》日本刑法學會,修正準備草案,刑法雜志11卷2號(1961)116頁~117頁。 )”
總之,所有的人類活動都伴隨不可避免的事故死亡(剝奪生命的過程),所以,其中僅是死刑把過失的危險作為理由而應該廢除,這不成立。
針對這一論點,三原憲三教授說道:“只要是保留論者也說到的回避‘誤判的可能’是不可能的,死刑將應該廢除”,同時對于竹田博士的見解作出批判如下:
“認為是少有的誤判從龜田案件開始,連著發生了三起。論者們主張說現代犯罪的證明方法逐漸地合理化、科學化了,但是不是在刑事司法的結構上有產生誤判的土壤呢?(注:三原,前列注⑤168頁、169頁。)”
這位三原教授的批判是關于回避誤判之不可能性其本身的內容,即使說其內容是妥當的,但假定基本沒有對應于前述竹田博士主張的話,還不能成為針對它的反論。而且,在刑事司法上有“產生誤判的土壤”的話,糾正它才是先決問題,而它也不是僅僅關聯死刑的問題。豈但如此,對于三原教授的那種見解,渥美東洋教授的下述指摘,作為反論是重要的。
“確實,按說是期望十分慎重而作出判決的死刑案件,被認為是誤判,這點會在誤判死刑上成為根據吧。然而,在日本,已確定的死刑案件,長久不執行死刑,因此留下了重審機會,法律的實際運用受到注意的事例不少。這和鎮壓反體制者那樣的國家,以及推遲執行已確定的死刑的各國不同,在日本,在命令執行死刑的法務大臣為首長的法務省里,實際上,關于確定死刑判決的問題重點,進行慎重研究的例行實務已經固定下來,這卻出人意料地為人所不知。刑事訴訟法第47條第2 款雖明文規定在死刑確定后六個月以內法務大臣應該發出執行命令,但考慮到重審和非常上訴,對于法的”平衡“的要求,有請求重審、提出非常上訴,請求恩赦,到這些程序終結為止,還規定從這”六個月“期間里減掉。再有,在多數情況下,其犯人的共同被告人刑罰被確定之前的期限,也定為不計入這”六個月“的期限之內。”“留給上面談到的法務省和檢察官的死刑確定后的程序方針策略,確實一直回避了由于誤判的死刑執行(注:渥美東洋《想一想我國的死刑制度》法律論壇43卷8 號(1990)27頁~28頁。另外,參照同《日本現行的死刑制度應該被廢除嗎?》刑法雜志35卷1號(1995)108頁。)。”
據這個意思來看,可以看出確定死刑案件的重審無罪的連續出現,是防止由于誤判執行死刑的刑事訴訟的規定和運用有效地發揮作用的結果。當然,這件事情,不是可以忽視誤判造成的死刑由于原被告人等關系人難以描述的努力才好不容易得以避開了的事實(注:龜田榮《死刑制度之存廢》龍谷法學28卷1號(1995)89—99頁參照。)。再說, 也并不意味著誤判死刑是經常可以避開的事情。
3.誤判,不限于和死刑之間的關系,必須避開。可是,由于生命的份量,特別應該是能夠最大限度地回避誤判的死刑,考慮設計出更能極限化的程序和運用。
盡管如此,社會的所有制度不可能是完善的,不能回避其過失這點也并不是就應該成為廢除、禁止該制度、該行為的理由。擴大行動自由也好,充實防止犯罪制度也好,由于其活動領域的擴充,必然伴隨擴大基于事故、過失的死傷。在這個意義上,在這里也將能夠承認“被容許的危險”的法理。(注:參照長井圓,交通刑法和過失主犯論(1995)153頁、175頁。)(注:參照霍歇·約恩帕爾特《現在正在廢除之中的死刑制度應該廢除嗎?》上智法學論集25卷1號(1981)21頁。 )伴隨新技術的一般性危險(risk),同時也擴大了自由而提高了生命的質量,在維持生命和健康方面也起著作用。現在正在努力整頓和改善能夠防止其一般性以及具體危險的各式各樣技術、程序、法規,并克服其弊害。這樣也不能把由于發生過失的死傷為理由,就斷定應該廢除該制度整體。這一點,也將適合于刑事審判和死刑制度。
然而,如果認為“被容許的危險的法理”是一種“利益衡量”的法理,對于一定制度、行為的正當化、合法化來說,“利害得失”就是決定性的。前述的由于回避誤判的死刑而擴充程序,也收斂于這個“利益衡量”的問題。死刑很容易被認為執行費用很少就可以解決問題,但為了避免由于過失的喪失生命應該最大的限度地重復慎重的刑事程序,所以就是限于為此的費用,也變成巨大數額。因為要剝奪最應該尊重的“生命”而以龐大的司法費用支持“死刑”這種“雙重犧牲”果真能符合“利益衡量”嗎?
進而,在把“過失死亡”和“故意殺死”兩者同樣看待時,會對把交通事故死亡和誤判死刑兩者等同視之而容忍的見解產生批判。對此也可以反論,駕駛也好審判也好都是故意作出,事故也好誤判也好都是以過失乃至不可抗拒力量作出,作為制度整體來說是起因于“不能回避的過失”而招致死亡,在這點上是一樣的。可是,死刑是所謂“計劃性殺人”,和駕駛行為根本不同。因此,就是在這里,同“被容許的危險的法理”之間的關系出現問題。它并不是危險行為究竟是故意還是過失的哪一個的問題,而是有沒有能夠回避其危險(risk)的“代替手段”。唯有它被否定的情況之下,作為“被容許的危險”,一定的制度、行為才能合法化。在死刑上缺乏其應該達到完成的效用(制止犯罪),如果以其他的刑罰手段也能達到完成目的的話,由于缺乏其“必要性”,死刑將不能作為“被容許的危險”而違法阻擋。
不論怎么講,這樣的歸結,因為死刑是剝奪生命,是從不能回避“個人的尊嚴”問題產生的問題,而并不是從誤判不能回避產生的。假定“不能回避誤判”它本身是問題的話,則不限于死刑,就是其他刑罰,也是產生“由于誤判侵害個人尊嚴”的問題的。因此,“以誤判為理由的廢除死刑論”,在這個意義上來說,仍不能說是妥當的。